妆发 杨益浩 灯光 杨耀 修图 高豆

2005 年 9 月 3 日,一支成立仅四个月的后摇乐队在湖南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 「在飞翔的梦境中离开」 的演出,在48V 乐队的台下, 15 岁的高嘉丰看着演出中的四位成员和一台台式电脑,深受震动:这是当时还沉溺于朋克音乐里的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和科技相结合的魅力,这一启蒙性力量也在后续的十几年中持续引领着高嘉丰在音乐领域内前进的方向。
在当时的长沙,地下音乐场景中主要有两个据点, 「在46Livehouse ,你可以看到最受欢迎的音乐人的演出,而 Freedom House 则 是 Alternative 音 乐 的 领 地。」从开业的第一天起,高嘉丰就混迹在这个 「神奇」 的俱乐部中,老板勇哥曾是千禧年前后一支后摇乐队的成员,并且极度痴迷于爵士乐 — Freedom House 的名字就取自 「自由爵士 ( Free Jazz ) 」 ,而俱乐部里的演出形式十分多样,广泛接纳了从电子乐到噪音摇滚等诸多流派,为刚刚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高嘉丰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灵感。
早在高中时期,高嘉丰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也先后尝试过朋克、后摇等不同音乐风格,并且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制作音乐;尽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始终未曾远离过音乐创作领域。金融学背景的高嘉丰在进入银行工作之后,不满足于 「周末音乐人」 身份,于是前往纽约大学进修音乐科技 Music Technology 的硕士学位。在纽约求学期间,除了钻研课程相关的音乐技术等内容,高嘉丰还深入当地的独立音乐场景中,从事实验音乐创作与即兴演出占据了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同样强调执行,实验音乐与自由爵士其实只有一墙之隔。」强调摒弃作曲家的 「控制」 , 崇尚音乐的 「民主」 和「自由」 而将注意力灌注在演奏者的实时创作中,高嘉丰在这一时期积累下了丰厚的演出经验以及音乐灵感;但是很快,深入地下实验音乐文化中的他对周遭不少同行的创作动机产生了怀疑: 「大家都在宣称着所有音乐形式应当平等,但如果你给他们一些悦耳的东西,他们又没有办法接受。 Discriminate 一种音乐仅仅是因为它好听,我觉得非常可笑。」
「我在纽约看到的音乐实验,本质上说和 1960 年代的实验没有太大区别,没有进步。它因为承载着太多需要 『挣脱』 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拘束让它成为了限制自己的枷锁。所有反抗运动都需要在时代的框架下理解,如今的音乐实验则失去了这样去解读的意义。」 高嘉丰解释道。
一个决绝的转身告别严肃音乐,开始拥抱受人欢迎的主流音乐形式和创作 「好听的声音」 成为高嘉丰的反抗方式: 「我只是想反抗这个现象,而非整个场景 — 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好了,时间会说明一切。」 出于对环境的厌倦,再加上想创作 「好听的中文音乐」 ,高嘉丰在毕业后选择回到国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音乐路线开始发生转变。
高嘉丰把自己在纽约时期的创作经验与回国后的生活经历相结合,创作出 《蹦迪治大病》 和 《报菜名》 等一系作品,意外受到了大量好评与追捧:不仅在于音色和音乐形式的革新,歌曲中的愉悦氛围令他从时下井喷的一众说唱歌手和电子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尽管在呈现方式上仍然带有音乐试验的色彩,但他的作品始终游离于不同音乐风格的边缘,却深得诸多音乐形式精要。
谈及不同音乐元素的提取与组合,高嘉丰提到了一个给予了他重大启发的音乐单位: six impala 。 这是一支遍布全球的乐队,成员们散落于世界各地,在线上协同工作,他们的作品如同切碎了的声音片段的重组, 「不是 『融合』 而是 『混合』 — 就像一只水桶, 里面装满了水银、羊毛、建筑废物以及阳光。」
2020 年, 高嘉丰出人意料地参与了当时最受热议的说唱主题选秀节目 《中国新说唱》 ,尽管最终没有成功突围,但他仍然以一段 「无配乐诗朗诵」 和强烈视觉元素的着装风格还是给观众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在回忆起参与节目的初衷,他却说: 「其实我和 Hip-Hop 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当时我只是对 『说唱』 感兴趣 —因为我也是一个跟风的人,我也知道我与类型节目不相恰,所以更希望在这里面扮演一个 『夸张』 的角色。」
比起节目中被吴亦凡称为 「外星人」 的浮夸着装,平日里的高嘉丰很少穿着这样风格的服饰,简单的素色 T 恤、短裤和拖鞋构成了他夏日最常着用的造型: 「你可以把前者理解为我的 『营业』 状态,虽然演出时的那个人也叫做高嘉丰,但他和平时的高嘉丰是有区别的。」
早在当代艺术盛行的纽约进行实验即兴的时期,高嘉丰首次意识到在舞台上单纯制造 「声音」 已经不能满足自 己 的 表 达 欲, 于 是 开 始 寻 求 通 过 视 觉 进 行 「 MusicOriented 」 输出的途径。在纵观行为艺术、剧场演出等不同呈现形式之后,他为自己制定下了颇具未来感的视觉语言: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种音乐人想要掌握更多主动权的 『驱动』 。 有的音乐人可以满足于作品的被动收听,但我觉得有时候音乐说不完所有的东西,这就需要视觉作为补充,将观点进行完整的输出。」
在开启了对视觉表达的追求之后,高嘉丰自然也与时尚领域产生了联结。利用纽约求学时期掌握的配乐知识,高嘉丰为好友的品牌 Sirloin 2018 秋冬秀场创作了配乐: 「我们收集了不同品牌广告的音乐,共同组合成一整场秀的配乐。那次的走秀令人印象深刻,模特穿着绿色的皮肤衣,通过绿幕技术,大家在手机上就只看到衣服在空中飘荡。」去年,高嘉丰受邀观看了国内独立设计师品牌 STAFFONLY的走秀,并结识了品牌的主理人兼设计师温雅。 当后者从金融行业中汲取灵感创作出 STAFFONLY 2021 秋冬男装系列,并开始给秀场寻求配乐时,就邀请到高嘉丰操刀为这场名为 「 TAKE THE BULL BY ITS HORNS 」 的走秀打造了一系列以刀剑声音采样和自由吉他演奏的配乐,在现场营造出肃杀、萧条的氛围。
除了通过配乐的方式参与时尚行业,高嘉丰认为自己和这一领域并没有什么交集,而他所打造的一系列抢眼的造型,则是因为 「选择有很多,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这样的视觉元素不太无聊罢了」 。舞台上的高嘉丰以大量带有金属质感和荧光色彩的装束著称,这样带有浓烈千禧年前后「 Y2K 」 风格的视觉语言也在他上一张专辑 《幻爱锐舞会Emotional Dance Music 》 中进一步得到了确立。
这张收录了 10 首歌曲的专辑可能是 2020 年华语音乐领域最独特的作品,高嘉丰除了大量采用了千禧年前后的舞曲合成器音色,还通过合作音乐人朱婧汐 Akini Jing 、养鸡以及 felicita 的演绎,呈现出 Hyper Pop 音乐和范流行化的 Y2K 美学相结合的气质。
在专辑进度行至将半的时候,异想天开的高嘉丰又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要将新歌做成千禧年前后所流行的跳舞机音乐的感觉,于是他以开源游戏 StepMania 为架构,写入了自己的新歌并成功制作出了一块 「跳舞毯」 ,并将其以实体专辑的形式推出。高嘉丰也将这份特殊的 「唱片」带到了演出现场 — 当他在台上演唱新作的时候,作为背景的屏幕上正播放着跳舞机的复古画面,来看演出的人们就可以按照箭头的指示舞动身体。
至此, 《幻爱锐舞会 Emotional Dance Music 》 专辑中的 Y2K 元素满得好像要溢出来,而高嘉丰却说: 「任何影响过我的东西,都会写在我的简历里。 Y2K 对我而言,只是现在所使用的工具而已。有的音乐人会为一种风格奋斗终身,而我则一直认为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风格和形式,都可以是我的表达工具。但我会根据作品产出的时代背景来挑选我的语气,不是语境,是语气。」 或许这就很好地解释了高嘉丰的音乐中元素为何如此丰富:总是游离于诸多繁杂音乐流派之外,拮取其中适合自己的呈现方式或者片段,对想要表达的观点进行诠释。
作为一个千禧年的亲历者,高嘉丰也曾一度迷恋于这种强烈的视觉风格,而在具备有独立创作的能力之后,面对着Y2K 的回潮,他对这种有着独特时代色彩的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也提出了自己的顾虑:比起社会结构更简单的千禧年前后,如今的 Y2K 风格中多了些许戏谑、讽刺以及黑色幽默。「在千禧年,它处于一个 『纯粹』 的状态下,就像青春期的恋爱,大家会把好的东西描述成 『天使』 ,把坏的东西描述成 『恶魔』 ,那是它最后的纯真时代;如今大家好像却都在用复古来逃避、反抗现下存在的某些东西。」
「模仿过去与真正的过去总是有偏差,复古浪潮大都以 20 年为一个单位进行 — 2010 年的时候人们怀念 1990 年代,2020 年的时候又开始回看千禧年。我们似乎总是喜欢挖掘小时候所崇尚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复古』的过程中,又会加入一些新的理解:再来一遍,总是会和第一遍有所不同。」早在 2018 年的一首歌里,高嘉丰就曾写下「不要相信那些复古派对,他们只是换个气氛暧昧」的歌词。
「随着这样的复古轨迹运行得越来越快,人类总是没有办法 『复』 昨天的 『古』 , Y2K 和任何一种流行元素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风潮中,我都会留意其中我所喜欢的 『语气』 ,如果下一个 『语气』 不是我喜欢的,那到时候也许我会去做点别的东西。」 高嘉丰预言。
静观 Y2K 出现的时机与它的再度回潮,二者出现的时机都被直观地与科技连接在一起。「这是第一次,科技力量被崇拜式地放在了美学中」 ,在此之前,则是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 超过半个世纪的酝酿,直到千禧年前后的互联网爆炸并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提速的网络缩短了人们和未来之间的距离, Y2K 就诞生在这样的情绪中: 「我们不知道科技会加强我们,还是会吞噬我们,这是一种面对未来,既感到恐惧又觉得兴奋的情绪。」
时隔 20 年后,在经过了漫长的科技内化过程,伴随着新一次的科技跃进与 「提速」 — 5G 通信、 超导材料和Starlink 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过程,当人们不得不再度面对一个极有可能快速变得面目全非的未来世界时, Y2K 理所当然地回到了主流视野。
当被问到 「你是否崇拜科技」 时,这位充满未来感的音乐人却说: 「人性与科技力量总是在博弈,我只是个旁观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艺术家们总是乐于讨论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精神状态,而观察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也同样启发着高嘉丰的艺术创作。今年,高嘉丰受邀前往微软位于北京总部的实验室,参与了一项 AI 技术的展示,在观看了 AI 创作的音乐作品之后,他进一步认定了 「人」 在艺术创作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我其实并不是 AI 技术的狂热支持者,始终觉得它就像缺了一粒沙子的金字塔,人们一直试图在教给人工智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这一定是有限的。」
「我的造物 VS 我的造物的造物,我选择了前者,因为我觉得有生之年我所创造的东西肯定能干得过它。」 高嘉丰笑着说。
「谈及科技,还必须要说的一个音乐人是 SOPHIE ,她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将声音与音色重组,还在频段的维度上解构了声音。 在 Hyper Pop 领域中创造出了所有人都没听过的声音。」 在这样的启发下,高嘉丰于今年 3 月以NFT 的形式发布了一段音频作品 《 Emotional DanceMusic (Spectrogram Signature) 》 , 并最终在交易平台 Opensea 上以 1.01 个以太币的价格被成功拍下,成为国内首个使用 NFT 这一 2021 最受热议艺术科技形式发布作品的音乐人。
「我想知道一段音频里能 『压缩』 进去多少信息, 于是我在一段时长 7 秒的音频中以波形的方式刻上了我的Logo 。 我相信声音是三维的结构,在每一帧的截面上都可以进行平面内容的创作。尽管现在我们仍然需要通过解码器来解读它,但也许在未来,人脑会完成这一工作。」在人与科技的夹缝中,高嘉丰始终在向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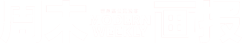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